媒体报道,也许是时候打造一个“猩猩人”了,猩猩人(humanzee)不仅有科学上的可能性,而且也能从道德上进行辩护。虽然听起来有点拗口,但确实没有理由说人类无法(或不大可能)在实验室里造出人类和黑猩猩的杂交后代(或称嵌合体)。

玛丽·雪莱的名著《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封面

伊里亚·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Ilya Ivanovich Ivanov)不仅对不同物种的杂交有着浓厚兴趣,而且还是家畜人工授精技术的奠基人,在马匹育种领域是世界知名的先驱
毕竟,根据生物学家的估计,人类和黑猩猩(以及倭黑猩猩)有大约99%的核DNA是相同的。即使这1%的差异中含有一些关键的对偶基因,我们也可以利用最新的基因编辑工具CRISPR,根据需要增加或删除目标基因。因此,制造出“猩猩人”并非遥不可及。这样造出来的个体既非人类也非黑猩猩,也不是人类和黑猩猩二者精确等分的结合,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如果这样的预测还不够惊人,那接下来我们还将论述一个更加充满争议的观点:制造猩猩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意,将带来许多好处。
从弗兰肯斯坦说起
2018年正好是玛丽·雪莱的名著《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诞生200周年。这部小说的副标题是“现代普罗米修斯”(the modern Prometheus),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史中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难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普罗米修斯式的傲慢只能带来灾难,而这不正是小说中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所作所为给我们的教训吗?然而,现在还有其他一些灾难正在上演着,比如对非人类动物的各种不合理虐待。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长期以来神学驱动的最具伤害力的一个神话:人类与自然世界其他部分是不连续的,因为我们是被特别创造出来、被赋予灵魂的,而“它们”——其他所有生物——则不是。
当然,我们所知的生物演化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但演化最基本的要点就是连续性。事实上,正是由于连续性的存在,才使“猩猩人”的出现成为可能。而且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基本要点应该会让人们认识到不连续性神话——即认为人类凌驾于所有其他生物之上——的破坏性。已经有无数的证据证实了人类演化的连续性,包括但不限于生理学、遗传学、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最顽固的不连续性支持者在面对一个真实的、功能正常的猩猩人时,还能继续保持这一立场。
当然,这一提议也有可能是双重幻想,不仅在生物学的可行性方面,而且这种“创造”能否产生上述冲击或影响,也得打上问号。众所周知,黑猩猩与人类非常相似:它们会制作和使用工具,能参与复杂的社会行为(包括复杂的交流手段和长时间的育幼行为);它们会大笑,会悲伤,并且在冲突之后能坚决地和好。它们甚至长得很像我们。尽管这些特征使许多人对马戏团表演、实验室试验等过程中对黑猩猩——以及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虐待感到愤怒,但并没有对捕猎、囚禁以及食用其他动物物种(包括黑猩猩在内)产生显著的阻力。这些动物在大部分人看来依然是“他者”,而不是“我们自己”。在赤道非洲的部分地区,黑猩猩还被视为“丛林肉”中颇具价值的组成部分,遭到许多人的捕食。
大卫·利文斯顿·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在《非人:为何我们会贬低、奴役、伤害他人》(Less Than Human: Why We Demean, Enslave, and Exterminate Others)一书中对伴随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进行了检视,揭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模式,即尽管人们承认其他人看起来是人类,但往往坚持认为他们在“本质”——无论指的是什么——上还不足以称为“人”。因此,即使我们与其他生物在演化上的连续性不可否认,一些顽固的偏见也可能继续存在。此外,一些人往往会掩盖不愿面对的事实:据说当伍斯特主教的妻子听说达尔文的理论时曾惊叫道“猿猴的后裔?我的天呐,希望这不是真的,但如果这是真的,希望不会有太多人知道!”
另一方面,当面对明显介于人类和猿类之间的个体时,一些人可能会痛苦地发现,二者之间的严格区分已经明显不再成立。但是,如果这些假想中的不幸个体真的被制造出来呢?既不是鱼类,也不是禽鸟,他们是否会发现自己的模糊处境和作为“初级产品”的悲剧命运,并且注定要忍受生物学和社会学上的不确定性?这是可能的,但值得商榷的是,通过牺牲少数个体使人类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自然属性其实是值得的。此外,这些个体其实是否真的如此不幸,同样也值得讨论。可能有的猩猩人个体会因为无法写诗或编程而感到挫败,但同样也可能有个体会因为能够在树枝间摇荡而喜悦。更重要的是,对目前还坚持认为人类具有物种特殊性——这样的观念对数以百万计的物种造成了伤害——的任何人来说,猩猩人的出现将扩展他们的认知并打破成见。
杂交体和嵌合体
在生物学的早期岁月,特殊创造论还占据着主导地位。许多人认为物种是严格固定的,每一种都是特殊的创造。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更合理的解释,每个物种都是一群能够自然交配并繁殖出具生殖能力后代的个体;也就是说,群体内的基因会进行常规性的交换。而且,虽然人们往往以“是或否”的两分法来看待物种,但物种之间的界线其实相当灵活,一直在不断变动。例如,绿头鸭和针尾鸭经常杂交,产下足以令经验丰富的观鸟者困惑不解的后代。灰熊和北极熊偶尔也会杂交,产生具有完整生殖能力的灰北极熊。
近期一项对渡鸦(鸦科分布最广的一类,分布于北半球大片区域)基因组的研究显示,这一物种此前曾分化为两个物种,较小的物种种群只局限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后来,这两个物种在几十万年前又合并为一个物种,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学名为Corvus corax的渡鸦。这种“分化逆转”(speciation reversal)现象可能远比我们原先想象的更为普遍。有证据显示,在乳齿象灭绝之前,它们曾与大象有过杂交。灰狼、郊狼和家犬在近几十年里也有过杂交记录。还有研究揭示,一些现代智人群体中含有多达5%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有些人可能还具有丹尼索瓦人的少量遗传痕迹。普林斯顿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罗斯玛丽·格兰特(Rosemary Grant)曾与丈夫彼得·格兰特(Peter Grant)一起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鸟进行了长期研究,指出许多动物物种(包括人类本身)很可能一直受到过往杂交历史的影响。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人类和黑猩猩的结合可能预示着我们将迎来某种生物学上全新的事物,或者威胁。
杂交体是来自不同遗传祖先的个体之间交配产生的后代,这意味着本质上几乎所有人都是杂交体,除了克隆人、同卵双胞胎,或许近亲相交的后代也可以算上。当我们谈及杂交时,主要还是指不同亚种的成员混种的过程,比如用拉布拉多犬和贵宾狗杂交,产生拉布拉多贵宾狗;更少见的情况是不同物种之间的交配,它们所产生的杂交体通常无法生存,或者不具备生殖能力,比如马和驴杂交产生的骡子,或者老虎和狮子杂交产生的虎狮兽或狮虎兽。杂交体是基因的混合体,其所有体细胞本质上都含有来自各个亲本相同数量的DNA。当然,所有有性繁殖的后代都是如此,只是杂交体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比一般父母更远一些。
另一方面,嵌合体的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它们来源于类似嫁接的过程,两个遗传系(最有趣的是不同物种)结合起来,产生一个部分属于一种基因型,部分属于另一种基因型的个体,这取决于取样的是哪些细胞,以及在胚胎发育期间提取细胞的时间点。可能是因为人类更容易想象将不同动物的可识别部位组合起来所产生各种猎奇动物,而不是介于中间状态的混血动物,因此长期以来,嵌合体要比杂交体更能满足人们的想象。印度教神话中的象头神(Ganesh)就长着大象头的嵌合体;同样的还有西方神话中的半人马(centaur,又称人头马)。嵌合体又被称为“喀迈拉”(chimera),指的是希腊神话中一种会喷火的怪物,传说它上半身像狮子,尾巴像毒蛇,身体中间还长出一个山羊的头,有时面朝前方,有时面朝后方。
假想中的猩猩人将会是杂交体(人类和非人类配子的结合)还是嵌合体(通过基因操控等技术在实验室里实现),不同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其实,无论是哪种方式,人类和黑猩猩的混合体并不是新鲜的概念。
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为伊里亚·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Ilya Ivanovich Ivanov)的俄国生物学家似乎进行了第一次严肃的、科学意义上的培育人与黑猩猩杂交后代的尝试。伊万诺夫有着完美的履历:不仅因为他对不同物种的杂交有着浓厚兴趣,而且他还是家畜人工授精技术的奠基人,在马匹育种领域是世界知名的先驱。在他的工作取得成功之前,即使最名贵的种马和母马都只能通过传统的一对一爬跨的方式授精。伊万诺夫发现,通过对种马精液进行小心的稀释,再用器械对母马授精,一匹种马的精液最多时可以使500匹母马受孕。他的成就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轰动,但这些都比不上他接下来的尝试。
不过,这次尝试失败了。
实验最初是在医学灵长类动物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Medical Primatology)进行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灵长类研究中心,坐落于黑海沿岸的阿布哈兹共和国首都苏呼米——目前还属于格鲁吉亚的一个争议地区。在某一时期,这个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大的灵长类研究机构。据说斯大林也对这类研究很感兴趣。
对人类与非人类遗传物质的结合感兴趣的不仅有前苏联的生物学家,还有小说家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他最著名——至少在西方国家——的作品要属《大师与玛格丽特》(The Master and Margarita)。他还写了一部名为《狗心》(Heart of a Dog)的中篇小说,对苏联时期社会上的粗野、愚昧和荒谬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小说讲述了一个国际知名的医生为了进行改善人种的实验,将一个刚刚死去的酒鬼的脑垂体和睾丸移植到了一条流浪狗身上。这条流浪狗变得越来越像人,只是并没有因此获得人性。后来,这个狗“出身”的“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的”人得到了政府赏识,竟被任命为莫斯科公共卫生局清除流窜动物科的科长,致力于将所有“流窜的四足兽”(主要是猫)赶出城市。
类似的改造实验成为了苏联生物学界的一个标签,正如S.A。 Voronov所尝试的“返老返童疗法”,即通过移植类人猿的睾丸切片来使一些老年富人的生殖功能恢复正常,这些实验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就人类与类人猿的结合而言,只有伊万诺夫才进行了最为认真的尝试。在职业生涯早期,除了对马匹成功进行人工授精之外,伊万诺夫还培育出了多种多样的杂交动物,包括“斑马驴”(zeedonk)和多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小鼠、大鼠和豚鼠)的杂交后代。在20世纪90年代一部俄罗斯电视节目中,虚构的伊万诺夫作为主角,在剧中被塑造为“红色弗兰克斯坦”。
1910年,伊万诺夫在奥匈帝国格拉茨举行的世界动物学家大会(World Congress of Zoologists)上宣布,通过人工授精手段尝试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杂交是可能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著名的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赞助下,伊万诺夫来到科纳克里(几内亚首都,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一家实验室工作,尝试了用人类精子令雌性黑猩猩受精的实验,但都没有成功(我们并不确定这种授精是通过人工还是自然方式进行的,但推测应该是人工方式)。1929年,在新成立的苏呼米灵长类研究所,伊万诺夫将实验方向倒了过来,组织了5名女性志愿者接受黑猩猩和猩猩精液的受精实验(推测应该仍是通过人工授精方式)。然而不幸的是,实验所用的雄性类人猿在“捐献”精液之前死亡,原因不明,而伊万诺夫本人则因为政治问题受到指控,在1930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1932年3月,伊万诺夫去世,为他撰写讣闻的是后来闻名世界的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促使伊万诺夫尝试这些实验。或许正是某种可能性的诱惑,当你获得了十分高效的人工授精技术,就像手里拿着一把锤子,你看到的一切——包括来自人类和其他类人猿的卵细胞和精子——都像是钉子。或者,他也可能受到了政治因素的驱使,抑或是被名声所累;又或许,作为一个热心的布尔什维克无神论者,伊万诺夫十分期待能打破宗教的教条。
无论如何,伊万诺夫的故事在俄罗斯以外并不为人熟知。西方人更倾向于嘲笑这些故事,将其视为类似《猿人星球》的荒谬情节,或者猛烈抨击这种不道德的企图。这样的尝试似乎越来越有可行性。可以肯定的是,伊万诺夫粗糙的杂交尝试在今天看来注定没有结果,因为即使人类和黑猩猩的DNA相似程度极高,但人类拥有46条染色体,而黑猩猩是48条,二者的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并不能产生可生育的后代。
不过,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猩猩人的产生并非不可想象。生物医学领域的许多突破不仅强调了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连续性,也明确无误地表明人类能因此获得益处。目前有许多研究者在尝试利用动物身体来培育可供移植的器官(肾脏、肝脏等),猪是较为理想的目标物种之一。这些动物的遗传指纹与人类十分接近,其体内培育的器官能够被人体免疫系统接受,并能接替人类患者受损器官的功能。举例来说,人类的皮肤细胞能够经过生物化学手段诱导成为“多能干细胞”,具有分化成任何人体组织类型的能力。假如有人需要移植肝脏,就可以将这些细胞引入猪胚胎中,使其发育成可供移植的肝脏(首先需要利用CRISPR技术使胚胎的肝脏发育基因静默)。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就能获得一只人-猪嵌合体,它有着猪的身体,但体内长着人的肝脏。
在多年的反对声音之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于2016年8月宣布将暂停干细胞的研究,而这项研究有望治疗(甚至治愈)许多严重的人类疾病,比如肝硬化、糖尿病和帕金森氏症。目前(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禁止资助的是将人类干细胞注入灵长类动物胚胎的研究项目,而将干细胞注入成年动物还是允许的。只要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存在生物隔离的界线,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条线绝对是可以渗透的,不是彻底分隔的;而且这种界线更多是基于伦理和政治判断,而非科学和技术。所有想法都能实现,至于是不是应该实现,则是另一个问题。
生命权并非人类专利
可以预期的是,猩猩人的前景不仅很可能颇具争议,对许多人来说,这根本就是不道德的。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培育猩猩人不仅是道德的,而且具有深远的意义,即使这些研究不能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那些最坚决的人类中心主义者,那些诋毁动物、认为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还有那些认为只有人类自己具有神圣的地位,与其他生命形式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在面对介于人和非人之间的存在时心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
无论如何,坚持“人类是以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独一无二的、具有灵魂的物种,而其他生物只不过是没有灵魂的畜生”的观念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观念不仅会允许,甚至会鼓励人类以强硬、残忍的态度对待自然世界,特别是其他动物。这种自我满足的神话可以使一些人理直气壮地为工业农场里的可怕条件辩护,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不仅无法转身,精神上也饱受摧残。这种自我满足的神话还会使一些人把人类的胚胎置于特殊的位置,认为它们就像等待赋予灵魂的“人”一样,并给予特殊的法律和道德考量,而这些都是我们的非人类近亲无法获得的。这种自我满足的神话还会使一些人否认他们自身与其他生物之间无可辩驳的演化联系。
当人们提到“生命权”的概念时,通常指的就是人类的生命。这种严格的区分基于人类生命独一无二、与其他动物的生命截然不同的假设。然而,就生物学角度而言,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想清晰地说明这一点,还有什么比创造出既非人类,也非其他动物,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生物体更好、更明确的方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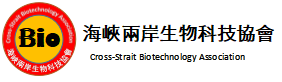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添加收藏
添加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